经济观察报 范世涛/文 伟大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哈佛大学经济系荣休教授、《短缺经济学》作者雅诺什·科尔奈(JanosKor-nai,1928-2021)于2021年10月18日在布达佩斯去世。消息传来时,中国“电荒”(电力供不应求的短缺状态)正在流行。这自然引起学界的议论:“电荒”的流行,是否意味着短缺经济学在中国的回归?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重温《短缺经济学》。这本书是科尔奈漫长著述生涯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也是他诸种名著里在中国传播最广的一部。
重温短缺经济
科尔奈的作品根植于他在匈牙利的经历。他曾告诉中国读者:“我始终是一位匈牙利的经济学家:激发我理论思想的灵感总是来自匈牙利的实践,而且我的建议也总是寻求帮助我自己的同胞。”
但科尔奈并不止于匈牙利。借助比较的方法,他致力于识别匈牙利常见经济现象所代表的经济一般特征。1980年,他在匈牙利和荷兰阿姆斯特丹NorthHolland出版社出版的《短缺经济学》(EconomicsofShortage)一书,正是这样一种方法论原则下完成的杰作。

早在195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科尔奈已经注意到匈牙利社会主义经济中广泛存在短缺问题,而将短缺提高到思考的中心,则得力于广泛的旅行和长期的思考。他35岁访问剑桥大学,第二年去伦敦经济学院,为英国的富足平静所震撼:
由于多年以来我一直生活在短缺经济中,因此与捷尔吉·彼得和米克洛什·吉迈什一样,伦敦富足宁静的生活以及充足的物质供应让我目瞪口呆。1963年短暂的剑桥之旅让我看到了英国人生活的一个缩影宏观经济学的论文,而现在我在伦敦生活了好几个月。当然我早在出国前就已经从学术资料中了解到英国与匈牙利在生活上的差异,但是从文字中得到的印象是一回事,从别人口中听到的情况是一回事,亲眼看到的景象则是另外一回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从那时开始真正学会如何使用“比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后来成为我的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标志)。我通常会从理论和统计学这两个角度对两种体系进行比较,但是激发我提出这些观点并且去证实它们的却是我本人对这两种体系的亲身经验。
凯恩斯建立现代宏观经济学时,面临的是资本主义世界需求不足的大萧条局势。而科尔奈面临的则是社会主义经济广泛、持续存在的消费品和生产品短缺问题。这也正是《短缺经济学》书名的由来。除了凯恩斯,这本书还受到马克思和赫希曼(AlbertOttoHirschman,1915-2012)的强烈影响。《资本论》“激发了我的无穷灵感”,识别和解释资本主义体系的功能失调,而这可以“深刻地反映出社会主义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赫希曼被放在与马克思、凯恩斯并列的位置,这有点意外,但科尔奈将短缺经济下的排队、囤积、等待等现象纳入严肃的经济分析,不是与赫希曼异曲同工吗?
《短缺经济学》分为上下两卷,分别讨论“没有价格下的调节”和“价格存在条件下的调节”。这两卷分别对应价格不变和价格变化但所起作用值得怀疑两种情况,下卷正是针对这种已经有所改革、价格机制仍受到广泛抑制的经济,隐含了对“天真改革派”的批评。
在短缺经济中,买方和卖方的地位并不平等,卖方处于有利地位。换句话说,企业而非家庭是这个经济体系运转的中枢角色。所以《短缺经济学》中对国有企业行为以及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有深入的讨论。其中创造性地使用了“软预算约束”概念。在微观经济学中,消费者和生产者都面临预算约束线,这条线不言自明、清晰给定。而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来说,这条预算线是可以移动的,借助国家补贴、税收、信贷和价格调整,企业预算约束可以放松变软。虽然软预算约束概念系科尔奈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时提出,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学中的通行概念,对研究财产权利、政府行为、金融危机等广泛的经济问题有着强大的解释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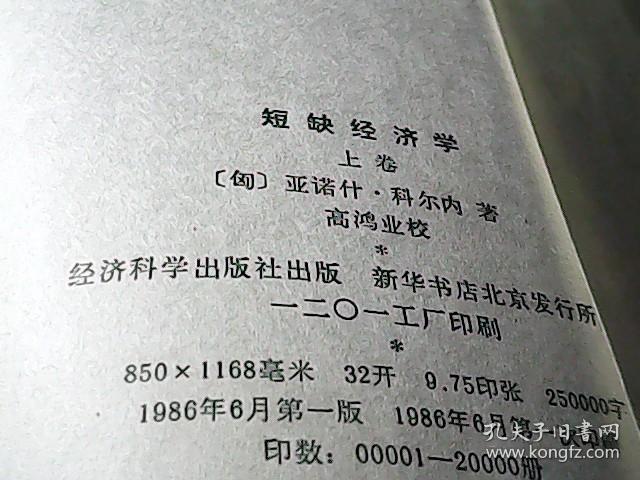
《短缺经济学》中译本1986年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出版社对出版这本书最初并不积极,社领导的第一反应与苏联经济学会会长一样,认为从书名来判断是“污蔑”。为此,经济研究所所长董辅礽专门打了电话后,出版社才转而表示支持,保证了该书顺利出版。此书第一次印刷为2万册,半年时间两次加印,到12月印数达到7.1万册。次年,《短缺经济学》荣获“1987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
《短缺经济学》中译本的出版,使科尔奈和这部书进一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共同话题。“非均衡”、“短缺”、“软预算约束”、“资源约束”以及“投资饥渴”等带有鲜明《短缺经济学》印记的词汇,开始在中国经济学界广泛流行,而8种科尔奈作品的译本在3年的时间内相继出版。当然,在现代经济学尚未普及的条件下,误解和不妥当地运用也随之流行,这些译本和错解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史的组成部分了。
“家长制”还是“父子关系”?
《短缺经济学》中译本的出版,使科尔奈作品的关键术语趋向统一。不过,这本书将“paternalism”一词译为“父爱主义”,这个译词并未统一起来,两种并行的译法分别是“家长制”和“父子关系”。
“父爱主义的程度”是《短缺经济学》的一章,该章聚焦于社会主义经济中政府(state,或译“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在科尔奈看来,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类似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国家对国有企业给予种种特殊地位并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国有企业则态度暧昧,一方面不满于家长式“父子关系”中的地位,谋求内部人控制(这里借用青木昌彦的词汇),一方面设法谋求国家的帮助。《短缺经济学》区分了从国有企业完全自立到被动接受国家拨给的实物这样五个不同的层级,指出这是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深层社会基础。

除了“父爱主义”,“paternalism”也被译作“家长制”。这个词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反复出现,中译本译为“家长制”,保持了与经典著作中译本的衔接一致。“家长制”概念又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传统衔接,这对理解现代中国的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颇为便利。钱颖一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发表的《科尔奈的理论与经济改革》一文,就使用了“家长制”的译法。
有的译者也则将“paternalism”译为“父子般关系”或“父子关系”。刘吉瑞和邱树芳是吴敬琏、陈吉元和荣敬本三位经济学家共同指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也是英文本《短缺经济学》国内最早的读者。他们1984年发表《〈短缺经济学〉简介》,即采用了“父子般关系”译法。(《〈短缺经济学〉简介》,《世界经济》,1984年12月)不久他们又将“般”字去掉,直接采用“父子关系”译名,这一译名得到吴敬琏的赞许。荣敬本是《资本论》中央编译局译本的译者之一,他和邱树芳、刘吉瑞合编的《短缺与改革——科尔内经济论文选》一书,就采用“父子关系”对译“paternalism”。“paternalism”原有父权的含义,又与中国“三纲五常”传统中的“父为子纲”衔接,也与科尔奈用这个概念表达市场化之后的国有企业一只眼睛盯着市场,一只眼睛盯着政府,但主要盯着政府的思想吻合,较“家长制”更为具体。
由于《短缺经济学》关于“paternal-ism”的章节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政企关系研究和软预算研究均有重要意义,这一术语又跨越经济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学科界限,期待学界群策群力,在既有翻译基础上,形成成熟稳定的统一译名。
鉴于《短缺经济学》只是科尔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30%,要了解他更全面的想法,就有必要去读解除自我审查后的《社会主义体制》以及此后的著作。其中,科尔奈的回忆录《思想的力量》尤其值得推荐,书中有专章回顾和总结《短缺经济学》的得失成败。正如青木昌彦指出,“这本书以敏锐的洞察力描述了匈牙利动荡不安的体制变迁过程和当代经济学思想的发展史——作者本人积极地参与了这两个历史进程。”《思想的力量》共有两个中译本:一本是《思想的力量——学术探索之旅的另类自传》,另一本是《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这两个中译本均斐然可读。
短缺经济学的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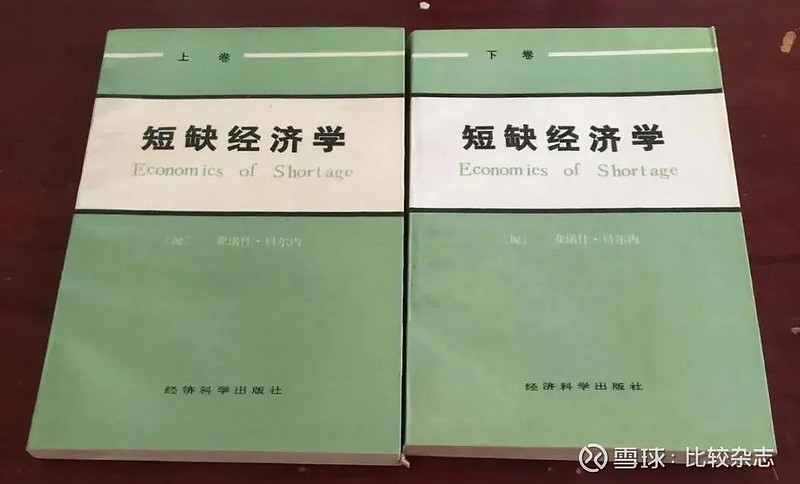
最后,回到文章开头所提出的问题,“电荒”是否意味着短缺经济学的回归?
科尔奈1985年为《短缺经济学》中文版所写的前言中写道:
改革过程的一个目标是要消除短缺。查看短缺状况是检验进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如果在经济的一个或另一个重要方面短缺消失了,这就是一个相当可靠的信号,即改革在那里成功了。如果短缺依然存在,这就表明改革还没有深入经济肌体的内部。
显然,按照科尔奈36年前写的这几句话,“电荒”的不断出现正是电力市场改革尚未深入经济肌体的信号,而赵人伟10年前针对“电荒”问题已经明确指出这一点。他这样写道:
我认为《短缺经济学》的分析是以没有价格信号和价格信号微弱为背景的。这些分析都属于国际经验,其警示作用是:要防止短缺的再现宏观经济学的论文,就必须注意价格信号的真实性。过度的和长时期的价格控制必然使价格信号失真,从而形成短缺。最近我国出现的电荒现象,尽管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但应该承认其中的价格控制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如果发电的原料煤炭已经涨价,对电价实行长期的控制必然要造成电力供应的短缺,即所谓“电荒”。正如有的评论所指出的,“市场煤”和“计划电”是不可能长期共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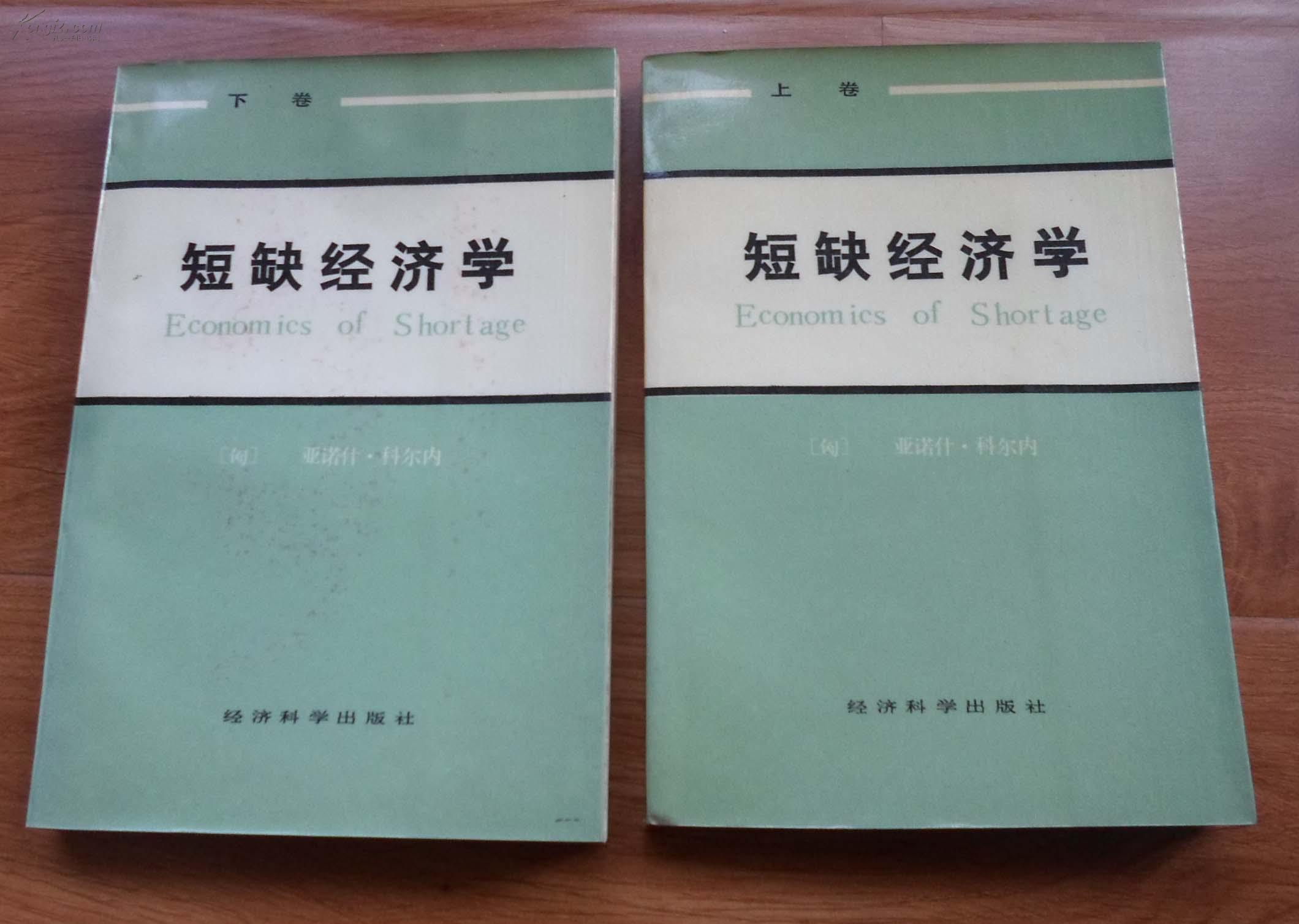
10年前,“市场煤”的煤炭价格升至1000元以上,“计划电”的政府管制价格仅联动上升30-40%,火电企业大面积亏损,形成一轮电荒:10年后,“市场煤”的煤炭价格再次上涨,高至2000元以上,而“计划电”的管制价格抑制电力价格上浮,火电企业再次大面积亏损,且发电越多、亏损越多,在秋冬之际以检修为由不约而同减少发电,就再现电力短缺的“电荒”了。“计划电”不能建立有效竞争的市场,在未来的某个年份也就无法避免“电荒”的重现。
更一般地说,在经济改革滞后的情况下,短缺、软预算约束、国有企业对国家和市场的双重依赖,会源源不断继续再产生出来,电力市场只是其中一例。进一步说,即使局部短缺通过改革得以消除,也不能一劳永逸地避免此类病症卷土重来。科尔奈希望经济学家摆脱幼稚的乐观主义,学习医生无所畏惧正视悲观事实的风度:几乎所有的人在一生中总有患病的时候,并且最后通常死于某种疾病。但是,这种悲观现实,正是医学研究和应用成就的推动力。科尔奈引用加缪的小说——《鼠疫》里的主人公列克斯医生和朋友的对话来表明这一点:“是的,”泰勒赞同说,“我能理解你,但是你的胜利总是暂时的,只能如此。”
列克斯似乎忧郁地说:“我早就了解到这一点,但是我不会因此放弃斗争。”
所以,科尔奈曾这样建议:完全理性的人、完善的市场、完美的计划、最优的社会制度的信仰和幻想,做扎实工作的经济学是绝不会相信和幻想这些的。世界经济正处于一种不景气的状态,没有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一切都会好转。我认为,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经济学家们有充分理由感到担忧、失望和不安。但这不应使他失去活力,屈服于现状。世界经济的状况和我们自己学科的现状,至少促使我们表现出应有的慎重,不再过分地无休止地发表不着边际的议论,老老实实承认我们的知识是有限的,为维护我们学科的名誉,当我们就如何医治生病的经济提出建议时,我们应该更为细致、更为审慎、更为全面。
既然经济痼疾要么还没治好、需要进一步治,要么治好了也说不定什么时候卷土重来,那么作为经济学史上的经济病理学著作,《短缺经济学》也就有常备案头、不断重温的必要。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