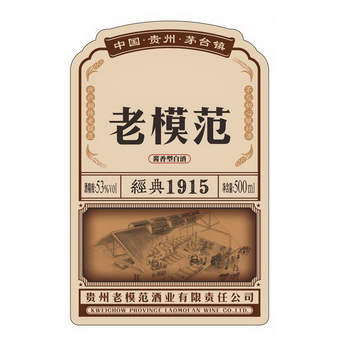һ�ἰ�廪Ӫ������Ϊ�������±������廪Ӫ������Ҫ˵��ȴ�Ǵ����廪Ӫ�����䱱�����������������ʱ����������ľ�Ӫ����ź�ֱ��Ǵ�����У�����Ϻ�������ѧ��ǰ������½��11ʦ�����ڵأ���70-80��������Ƕ�������11�꣬���廪Ӫ�������������֮�顣70���ĩ�Ĵ�Ժ���洦�ɼ���·���Ǹ��٣��پ�Ŀ�š���ץ���ι��������Ŀںţ�����ban���ҷ��ġ����������ռ���Ҳ�ܸߣ����ǼҾ���һ���������˲��ã����־Ͷ�Ī������ʧ�ˡ������������ǻ����������ˡ�
��Ժ���澰ɫ�������������࣬��������������Ӫ���ͼ���סլ����שƽ������·���ǰ���·��ˮ��ש���棬�����ſڳ��������ҷ�ˮ������ũ���ũ��ĸ���ϵͳ��768�����ﻧ���ľ��ã�����ֱ��������Դ��ÿ�����������������������ʱ�����ö��ľ�������ɢ���ڴ�Ժ��ÿλ���䡣��ʱ����Ϊ��Щ���뿪��Ժ�Ķ����������ǿ��Ƶ���������������������߿������е�������
��
��Ժ���ΰ�ͦ�ã�����ż�еĴ�ͽС����С���Ӵ��ˣ�����û����Щ������һ��Dz���һ������ҹ����Զ���߶���һ����ʱ·�����Ĵ�����ɭɭ�ģ����Ǵ�Ժ�����������࣬�紵���������Χ���Ͼ���������Ż��ˣ�����ֻ������ʵʵ���ڼ��������Ͽ���ӰƬ�����ս��Ƭ����ž�ս��ʤ���Ѿ���ͷ��ܣ��ǽ�һ������ӡ����̵Ļ��Ǿ��Ƭ����ʱ��С����ҲС�������صĴ���ץ�����Ͱ����ŵ�һ���㡣�������������ߣ����ֻ���ͷ����Ŀ�Ұĺ�����ȥ͵ȥ��ȥɱ��ȥ�ݻ��������ڶ��ʻ��ơ��������ǣ���Ԫ���ݵ���̫̫�ڰ��п��ӵľ�ͷ�����Ҳ�������������˵�Ѵ������Ե�Ůʬһ�������ľ�ͷ���Ҿ�ֻ�б��۵ķݶ��ˡ���Ƿ��켫���ǻ�Ƥ��ÿÿ��ͷ��ҹĻ����ʱ���϶�����״������������ӰƬʱ�Ҳ������һ��ʱ���DZ����۾��ģ��������п��������ϳ����ij��֣��е��˷���Դ�ˡ�̨������Ƭ��Ȼ��̬��ֻ�������ܹ���Ƭ���ĵ���ô���ˡ�������ʱû����ҹ����������Ƭ�ӣ������ҿ϶����������Ρ���Ȼ�ֲ������ǣ�ֱ������ҹ���û��ӰƬ�ּ��ƶ����������С��������80�����ӰƬԺ��������ĥ��
1982�꣬�������ڴ���ó�ӳ����������ɽ�˺���ʢ����ǰ��δ���й���������Ӿ��������û������˺ÿ���ӰƬ��һ���ӣ������������������ģ����̵�Ƭ��ֻ���ݾӵڶ��ˡ�
��һ�����ڴ�����ӰƬ�������������Ȼ���ص�֪ͨ������Ա�������ϣ�������Ϊ������Щ�����أ�����������������սʿ�ڶ������С�������ɧ�ң�Ҳ���Ǿ͵�ȡ�ĵĸ䰡���°���Щ�ģ����Ƶ����Ǻ���Ū���ģ�����Ҫ����ʿ��ǰȥ��ֹ���ƺ�Ҳû��˵���º����صĺ����
ÿ����գ�����ã����Ǻ���ķ��ݣ����滹��ӭ�����������գ���Ϸ��Щ�ģ���ӡ����̵���һ��ת�̣�ÿλ������д�Ų�ͬ�Ľ�Ʒ��������ת�����ĩ�Ƚ�����һ�顱����������������ֵߵ��ˡ��ھӹ����������Ǵ��������ĵ�Ա��������ʱ�ͽ��͵͵���ȥ���俴һЩ�ڲ�ս��Ƭ�������أ�����ͧ��ɽ����ʮ����Щ�ġ��������̳��棬����Ŀ��������������������õ����������������͵���ڲ�ӰƬ���������ǵ�ר����
�����������ѧ����������ʱ�䶼���ڶ�Է��ɹ��ġ���ʵ�л�Է�ƺ������࣬Ҳû�й����IJ�Ƥ�������òݴԸ����������������л���е��������ͦ�����dz������������Сè��ץ������Щ�ģ��������������棬�����������ε�����ʱ����û�ˣ���������������ˮ��������ˮ����Ϸ��ÿ���浽�������������ʪ�ˣ��ܹ������̫������ˮ��Դ�ˣ���˼һ�¡�
�����������������ܶ��������������ߵĺóԵĶ�������������֮������ͷ�㻨Ǯ���ޣ���ĸ�ֹܵĺ��ϲ������dz�ȥ���������ǻ�������ȴ����ʱ��Ӷࡣ�Ұְ־��Ƿ�����Ĺ�����Ա������Ľ���ƺ�����ʶ�ң���ȴֻ��ʶ���м����ˣ���ʱ���ص�С�غ��ߣ�ÿ�ζ��±����������������������ǻ���û���Ѷȣ������ֲ����⺰�Ŵ��������̣����Լ�ʹ��������������۸�������ʱ���ֹס������ת�����Ķ�Է����ȥ�ˡ����ҿ̹����ĵ��ǣ���һ���Լ��ڷ������Ժ��������ϰ࣬С�ֲ���ʵ����������������������һ���Ͼ�¯Ҥ���и�С���ţ������Ͳ��������С�����ǻ��ģ�û����Ҷ��������˫�ŵ�С��ָһ���Ӿͳ���С�����������������Ʒ������Ѫ��ģ�����۵������۳���������������ָ��ֺ�ǻ��Dz������ġ�

�������ﻹ��һ������Ĺ���д����ӣ�Ũü���ۣ�׳׳ʵʵ�����̷�����룬����������Ϳ��ӣ������Ħ�У�����80��ǰ��������ڳ������ˡ���ϲ��ŪС�������ڿ��ɿ���ץһ����Щ�ģ����Ƕ��е�������ǰ�տ������˵������£�˵��70�������һ����У���µĸ�������С������һ�٣����������ţ���ϧ�����Ϣ��30���Ż�֪�ģ����ź�����û���ֳ�Ŀ����һ�˷����ĵij��档
��г��Ǹ���ȥ����������������2���£�1.���ڵ��ǣ���������AK47���ڵ��ǣ���������54ʽ��ϻ�ģ�ǰ�߾ͳ�����Ʒ���һ���һ��δ�����54��ǹ���ڵ����ɼ���ʱ�����Ƚ�ƫ�ġ�2.��г�����������ɣ���֣�����ϲ��ȥ�ɺ����������ɣ��������÷���ԡ��������Ұ���ģ�û�˹�Ҳ��Υ�棬�Ҵ�ѧ��ǰ��Ȼ�ɵ�����3-4�꼶����û��Щ�£���ij���죬��ͬ�¿ظ���Ϊ��ѧ����Ա��������������÷����Ϊ������ϧ�е������������ҵĵ�Ա���֣��������ʦ����д���֣��ұ��к�ԩ����������������Щ������Ϊ��������ѹ�������ò�Υ��д��һ�ݼ��֣������ҵ��IJɲ�������ʦֻ�쵽һ�������Ϻ���ϵļ��־�pass�ˡ�
�ķֲ������Ǵ�Ժ���ھӣ����跭ǽ�ܹ���ȥ����ѧ�ϱ�Ժǽ���и�С�������������ͳ������ǵ���������������Ƹ����������ǧ����һ�����±�һ����˿�ŵ�����½��ѧԺ��˫�Ŷ���Сľ���ϵġ����족����������ӻ���ȥ�ɿ죬���Һ������ۣ���ϧ��ʼ��ûѧ�ᡣ��ʱ�����ķֲ���ʿ��ִ�ڣ������ǣ���������ſ��ǽͷ������ڱ��Ķ���ȫ�˲Ÿ�����ȥ������λ��Ƶġ�
�ӹ������ҼҺܽ���û�¾�ȥת�ƣ�������һ���ܴ�Ȳ֣�����ȥ�Ķ�ץ��ȸ��������Է�յĿռ��ڣ���ȸ�ٲ��Ǹ߸����Ͽ������ɼ��Ķ����ˣ����Ǻü��ζ���������ȸ�����ú��ݼ�����δ��������ͦ�����ˡ��ӹ����������һ̨��ɫ���ӣ��ڵ��Ӳ��ռ���������Ǽ�ֱ�Ǹ��������ǰ��쳣���ȥ������ӣ�ÿ�ζ���ɽ�˺���ԭ���Ͳ���ĵ��ӣ�������ǰ�������������������ף�������ô��������Ȼ���²�����ֹۿ���
����һ���ܽ��ӹ��������DZ������˷��ΰ�ĸ����dz������ҵ����ѿ�С���ĸ����������°࣬ʱ����һЩ�ܽ���Ʒ��ȥ�ӹ����ƺ��ǼƼ��ģ���Ҳ����ģ�����ظ�����С������ǰ���ë�̡�
��ȥ�ӹ����ĸ�������·����һ�����䣬���泣�����Ÿ��������ţ�⣬������������ģ������Һ��ɱΡ�
�ӹ����������к����ˮ�����ڹ��ھ������ɵؽ��š�������һ�ο��ڹ�ԣ����������ζ����������ʱ����ƶ�������ǶԳԱ������㽣���������⣬�һ��Թ����ڲ���ǰ�����ϵ����ͣ�����ȥͦ�ÿ���������Ƶģ���û��Щ��ζ������ѧ�Եİ��������е��𣩣��ֱߵĺ����죨�óԣ�����ư��ͦ�óԣ��������ἰ��ɽ���ȻҲ���óԵ����С��Ҹ�����ȥ������ľ���������·�ϣ�˳���ڽֱ�ժ�˼����㶹��ȥ���������˳ԣ��ڸв���������ժ�����е㵨ս�ľ�����Ȼ�ǡ�˳�����ġ�

��Ժ����Ľ��ͺͶ���768�����ٻ����������dz�����˵ij������������ǵ���Ҫ������İٻ��̵ꡣ768�Ĵ�һЩ���м���¥�ɣ����͵�С��ֻ��һ��ũ����̵ꡣ��ֻҪ����Ʒ�ĺͱ������������Ǿ���Ī����ջ�����ǵã���768�İٻ��̵���ߵ�����ϡ��̯����������죬�����˼�ëǮ����ϡ��������С�����϶���û�������ұ�����ʹ�õģ������£��ͷ�����ͳԣ�ͻȻ����һ���磬����ϡ��ճ�Ѵ����ҵ������ϣ����û�Ե����پ��������ס����͡��ˣ�����ʹ�����Ƕ��������ӵ꣬����������ǰ���̻����ڵĺ�ȥ�����������2��5һ����ϸϸ��ֽ�����Ķ��߽ţ���������յ�����С��������е�ʱ�����е�6��Ǯһ���������ס��ڴ�Ժ������ȥ�������̵��·�ϣ���һ�����Ķ���piaji����С�̣������������㣬�����ﻹ�е�ʱѪƴ�ijɹ������һ��ո�µĻ��Ķ��������ɴ��������������£����������壬ͦ��ͦȫ�ģ���������ģ�û��ü���СԲƬ���ⶫ�������ܶ����ˣ���֪����ղ��г����ܹ������ü۸�
��������һ��������˳�Ÿ���������һ��·����һ��С�Ľ����ӹ�����������ȥ����͵��Ƭ��������״������ʽ��״����ܹ������Ƶ�һ����Ƭ�����ֽ��������Ǹ���Щ�õġ�����ӵ��һ�����������Ƭ��Ҳ�治����Щ��������ֻ�������д�������û�еĶ���������һ���ڵ��ʱ����Ҽǵ�����Ь����Ժ��������������߷ŷ磬����2����ھӹ�������ȥ����Ƭ�����յ�����������Զ�����д����������ŵ�������Ķ��ӡ����ǻ����˰ѳ����ӵ�ƽ�ײ��ݷ��������ϣ����г�������ѹ����Բͷ��Ū�ɱ��ľ��Σ��������ʹ�ķ��컭�һ���������ֶ���һ������û�еı�������������ˡ����ҵ�ʱ��С�����Ǵ�ͳ�����ϵĺ���ѧ����ֱ��������������Dz��Եģ���ȷ���ܹ�������ײ��������ʼ��û������ʵ������
��Ӣ��
��Ժ���������������ۤ��ƽ�ˣ�����ͬ���ս�ѣ�����Ҳ��ȫʡս��Ӣ�ۣ�������ȫ�����Ĺ��������ۤ��������ͬ�����Ѽ���ѣ��ҳ�ȥ�����档������ʦ����Ա������������¥��¥��¥�£������ɣ�����Ҫ���Լ��������ˮ�ޣ��������ޱ����ۡ�
��Ӣ�ۼ����������йض��¼�����������ʹ�Ҷ�Ӣ�����ը�ﱤ����ֱ�۵���ζ�����һ���һ������Ķ��������绰����������֮���ü����̲�ס������ȥ������������������Ů���������������׳�Ҫ�������һ�仰����˵�����ŵذѵ绰����������������µغ����˼һᰴͼ��������������������뿪�����ҡ���ʱֻ�д�Ժ�ĸ߸ɲ��е绰�����������е绰�������ݻ�Ʒ�������ء����һ����������ʵĶ������������Ǻ������û�ȥһЩ�ͻ�ģ�ͺ��Ȼ����ڵ��Ǹ����棬�ҿ��˺�ϲ�����������������ܶ�������������ǵ�һ�������Ҽ����ģ�����ħ����������Ƭ����ʱ�������װ��ӡ��һֻ�������˵Ĵ�Ϻ���������죬����ȴ�Ҳ���Ϻ��Ӱ�ӣ������ɱΡ���ʱ�����ϰ����ֽ�IJ�һ������װ��һ��СϺ�ܽ�ģ�����ɫ���ͣ����ǰ������˺��˳�����Ȼû��һ��Ϻ����ζ��ͦ��ɥ�ġ�
��Ӣ�۵Ĵ���������ȥԡ�ؿ���������Ĵ����������Ǵ����к�������һ����������棬�����һ����ͦԶ���ѵþ�����ϱ��ص�ľЬ�ӣ����ö߷����µ��������ӡ��Ұ���ʱͦ����ģ���֪����Щ��ϵ�����Ҹ��������������������裬��һ�������ְ�Ĺ���Ա�����ϼ��쵼ʲô�ģ��ڹ�����С��ߺ����Ҫ���������ߣ��Ұ־þ�ɳ����û�����£����Ҹ����ŵö��ڲ�����ź�������ҳ���
��Ӣ���������ĺ����ӣ���ũ��������֫��̱�����ҷ���ͦ�ã�����ʼ�����浽���ϣ����˾��塣�ܶ�ý�屨�������ǵ��¼������ڸ߸����治�����㿷֮��ʵ��̫���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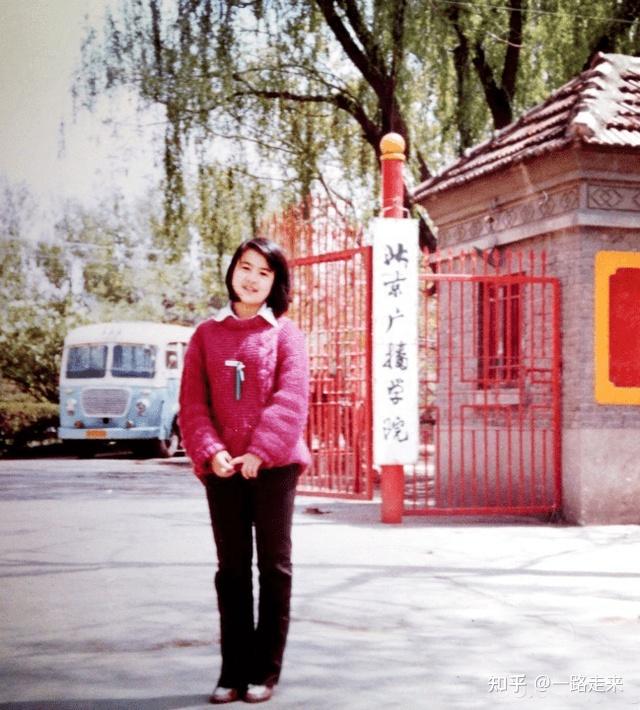
��Сʱ��д��ϰ������ֹһ�ν��������翴����Ӣ������·�ϴ�ɨ��Ҷ�������Լ����Ͷ������µ��������ƣ�̹��˵����һ�ζ�û�������������ʵĽ��������˿�������ڲ���Ӣ�۵�ΰ��
����
��Ժ�����ѧ������ѧ��֮ǰ�Ժ��ƺ��й�������ѧ���廪Ӫ��ѧ������������Ȼ�������꼶�����ڽ�����
��ѧ��������һ�𣬿��п���һ��Բ�Ρ��ƺ�ԭ���ǵ�����Ժ�����������̫̫�Ĺ��ݣ�����Ҳ��˵��̨���˸ǵġ����Dz��ݵ������ߣ�ľ����棬��Ư�������������ȥ��Сͬѧ�Dz俴��һ������ľż�ŵ�ľż�ݳ����dz�ϲ������ʱȥ����Ժ��Ļ����棬Ҳ�ܿ��ġ��ɼ�������ͷ����İ��û������벻����ʱ�ڵġ��ͼ�Ȥζ������½��ѧԺ��Ҳ��������������������û�Ϲ���һֱ���䱥���˺�����㽡�
��ѧǰ���и�С���ԣ��ͳ�һЩͼƬ�����ϣ�����һ��ͼƬ���ҿ��˿���˵����Ь�ģ��������ף���û��ȷ��˵���̵�������𰸣�����һ��ȱ��������Ķ�����ˡ���Ȼȫ���������ѧҲ��������ЩӰ�죬��Ȼ��Ժ����ô������ѧ����
1-2�꼶�Ľ�ʦ������ϴ��ˬ�ʿ�����������ʦ�����ǹԹԵر����������ڳ�����ʣ����������������ڶ��Իص�������������ǵ��������������Ƽӱ������������µ�ͽ�ֲٵij��������ߴ����Ӱ������ȥ��ʧ��
����ʦ������������ϰ�ߣ�һ�ǽ�ѡ����������ڽ��д�����ã����Ǽ�¼ÿһ�εĶ����ֲ����ʣ��������Ҷ���ֵ�����ѧ��ҵ��ֻ�ǵ�ʱ��Ȼ̫С���Խ������ÿһ�ζ��е�N��ġ��ĵصá����Բ����䷳��һһд�����ǣ�ÿ�ζ������۵�һ���㡣

��Ӣ�����ϲ���ľ��Ƿֽ�ɫ�ʶ���ÿ���Ҷ����־ٵø߸ߣ����������Լ��ֵ���ɫ�Ķײ�Ҫ̫�١���һ����ȫУ��ǰ��һλ�����ֽ�ɫ�ʶ�С���ӵĿ��ģ��ҵ�С���ӣ��������ף����ñ���ռ��ʵ�ݣ�������Ϊ��ˬ��
�ҵ���ѧ�ɼ���Ȼ������ϰ��Ҳ���ܺ�����ӡ�������һ���ǣ���дij�������������������ı�ʽ����ĩд�����ڻ�ȥ��·���һ��������ı�ʽ�ľ��ʳ������������ʦ��Ϊ����֮�ʣ���Ȼ��Ҳ�����õġ�
���ϰ�������ںڰ��Ϲ������Ķ���
������ʱ��ѧ�����㣬����ѧ��·�ϣ�������������ﻩ������ֱ�졣��ʱ���ס�������ȥ����ʲô�Ŀھ����ĺ��죬����Ҳ��÷ɿ졣��ϧ���ȫ�������ˡ�
У�������й�һ�β��ֵ������������һ���������ܽ�Ƥ���»��ֵ䷭�÷ɿ죬�Ҳ�һ������֣�����һ�������֣��һ�æ��ֻд�µ�һ���������ڵ�ҳ�����ѵڶ��������������ˣ�������еڶ���
һ�������ݳ���Ŀ���Һ�����˵СƷ������������������ģ���è���������������ˮ����ֹҹä֢��Щ�ģ�������һ�䡰���ŵ�Ͳ��ô�á�����ӡ����̡�����һ��¹����˺ܶ���̨�ʣ��ȱ����Ķ���������
�μ����dz���ռ�ǵ���Ϸ����������ֳ�����־���䣬Ҫ���м�����ͨ�������Է��Ƶ�����ͳ��֣��ı�����Ҵ���Ա�ѶԷ��Ľ��乥��ʤ�������������ƣ��߿ڴ�������Ȧ��ײ���ӣ��粽���������ǵ����

�Ҹ���ʱ��������3�꼶��ʼ�ֵ������ж����������涼�ܻ������Ͻ�����ͩ�Ѻ�Ӽ�ǵ���Ŀ������ǰé�����ǰ���ʦ���������Ǵ����㻨Ǯ���Ҵ��ǮҲ��ࣨ��ܼҳ�Ҫ�£��������Ҽ�����ѧ�Ͻ����һ�����������Ͽ��š��ȽϿ��Ƶľ��Ǻ������糿��һƬ����������6���͵�����ѧ������У����һ���ˡ��Ҿ��������ڿ�������Ź�ů���ﻩ����ˮ�����������У��������ǰ��¥�Ĺ��£�������Щ���ġ�
��ʵҲ�и��˵�ʱ�̣�������ʱ����������ѧ���澲�ŵ������У�ͻȻ��������������̧ͷһ�����߸ߵ������ϣ�һֻ��ľ��������������֦�����Ҳ��ɵ�����ۿ�������ֻ�����鱾�϶�����ֲ��˿̾�Ӳ������ͷ�ϵ������棬��ĺܿ��ġ�
�����༶��С�컨��ѡ��ѧϰ+�Ͷ�+�ۺϣ����ҵ�С�컨��Ȼ��࣬���ڵڶ�λ�ij�����һλ����С��������������ǰ����ʦȥ�����ϯһ��̫���������ȶ�������Ƕ�����������һ�ο��������ŵ��ݳ�������������ѧ�����ش������������������ҵ�ʱ�ľ����������֣����ޣ�����һ�������Ѫ���ڣ��˷ܰ����ɼ����ǵ���ѧ�ж�ô�����ˣ����������Ŷ�û�У�Ҳ�����к���У�Ӵ��Ļ��ᡣ�������ѧ����Ա��ʱ������ôһ�Ρ����ۡ��Ļ��ᡣ�ؼҵ�·�ϣ���ʦ�����Ƿ��˸ɵ���ԣ���ʱ�ѹ��緹�����������⵰������㰡������һ��ȱ����û��ˮ���֭���Ե�������Щ��ҭ��������ˮ���֭��̫�����ˡ�
������ʱ������ѧ�������£�����Ȼ�������¡�����ɪɪ�����죬�����켸������ȥ���ӵ���Ȧ��ɨ��������������һ��սʿ��û�У�ֻ�м�ͷ������������ŵض�ס�������е�ɨ�㡣���Ǽ�����ҧ���ǣ�������Ҳȷʵ�²�ȥ�ţ�ֻ������Χ�ݲ�ɨ�˼��¾ͻ����ˣ�û��Ŀ����Ҳ��û�п佱�ţ�ֻ���ҵ�ϰ������һ����ʵ���زĶ��ѡ�
��Ժ����ѧ����һ��������ѧû�е���ɫ�����ǡ�����Ժ�����������ɼ���Ʒѧ���ŵ�սʿ�����ǵ���ĩ��ϰԱ���������ǽ��и����������ľ���ȥ������Ͼ�ɽ��ɽ�����DZ��Ͼ���ˮ����������������֮��ĸ������Ŷӵ�ɽ��Զ��·��ȥ�Ͼ�ɽ�����������ï���кܶ��Ժ��������С���棬���dz�����ֻ���л�ȥ�档ÿ�γ�ϯ���ͽ�����Ƕ��ܼ���������ȫ���߳��������ˡ�
ÿ�����ڣ����Ƕ�Ҫ���ϰ��������̿㣬�жӲ���������Ӣ�ҹ�Ĺ�ĺ�����������ʿӢ�����£�ɨĹӢ��Ĺ�����ǰ���Ҳ�������Σ������ܿ�����ߵ���գ��ܳԵ�ƽ���Բ������ɿ������ɼ����ǵ�ʱ��ô�������㡣
������ѧ��������һ���Ҽ�����̵Ĵ��£����Ǵ�Ժ�����������ȥ�г������һ��С�ӱ���Ӿ������Ϸ������һ�����������ˮ���Ҳû���������������Ǻ��������������һ�������͵�ˮ�ף����Ժ����ͻ���ȥ�ˣ��ȵ�Ů���Ǿ��̵غ���սʿ���о��ˣ��̳���ֻ��һ�߱��������塣����¶���ѧ�Ĵܴ�ȫУ�������������������������ǵ����ֺ����Ҵ�Ķ��ӣ�վ��������ǰ����ͷ�����������䣬����У�쵼�ڴ�����������������ij��������л������˼�������Ҳ������ȥҰԡ�����ԭ����Υ������
�һ������Ѽ�һЩ���ѵ������ҵ���͵���ʦ�������ģ����������ô��Ǽ����ܶ������ǰ���д��ҵ�����ܼ�����ʦ��ѧȫ�����ĵĸ�������ʱû�в�ϰ����ͥ��ҵҲ���࣬���������°��Ŀ������ºö࣬�����ֽ�Ķ���������ġ�
ÿλ�꼶ֻ��2���࣬ÿ���30�ˣ����ھ���ô�൳Ա�ӵܣ������Ĵ����ѧ�����Ǻǡ���ʦ���ǵ�Ա�ļ�������ʦ�����������ȣ������Ļ���һ��Ҳ�ɣ���ʵ���Ƕ�������ô��С̯������˵�Ա�ﱲ��ѧ�ѵ����⡣���ײ�Ҳ�Ǻ������ģ�һ���ܹ�ģ���������ޣ���ѧ�豸Ƿȱ��������ܺ������Ŷ�û�У�ʦ���������㣬����罻�������������ѧˮƽ���ߣ�ֻ�DZ��ܱ�ũ������͵���ѧǿһЩ�����������ѧ����û���ȣ��������ڴ�Ժ��û��ѧУ�����Ը�����ʮ�꼶�Ķ��Ӵ�������·��ȥ���ߵĸ���ϵͳ�и��л��Զ���������ѧ�����������ܸ����˼ҵĽ��Ȳ�������Ӧ�Ƕ���ѧϰ�������һ��������ʮ���ʣ�¼��ٵļ�����ѧ��������������㷣��������ˡ��һ��ã�4�꼶�ͳɹ������ӡ���û�������鳤;����ȥ���תѧ�����